在天然道观的幽深之处,我听见了生与死之间的一段古老对话。它讲述了易经中对女人的性格暗示,那是关于柔韧与坚韧、温婉与强烈之间精妙平衡的故事。

我想起南宋李嵩《骷髅幻戏图》(骷髅团扇图),这次,我们讲一个恐怖的故事:南华真人庄子出游路过楚国时,在路边遇见了一颗枯骨突露,森森然在地的骷髅。庄子淡定地用马鞭敲了敲骷髅,开启了提问模式——于是恐怖故事变成了哲学对话:
“您是因何流落到如此悲惨的田地?”庄子问,“是贪求失道还是遭遇了天灾人祸?是作恶闯祸,怕累及家人而选择了自我了结?还是寿终正寝而安享了天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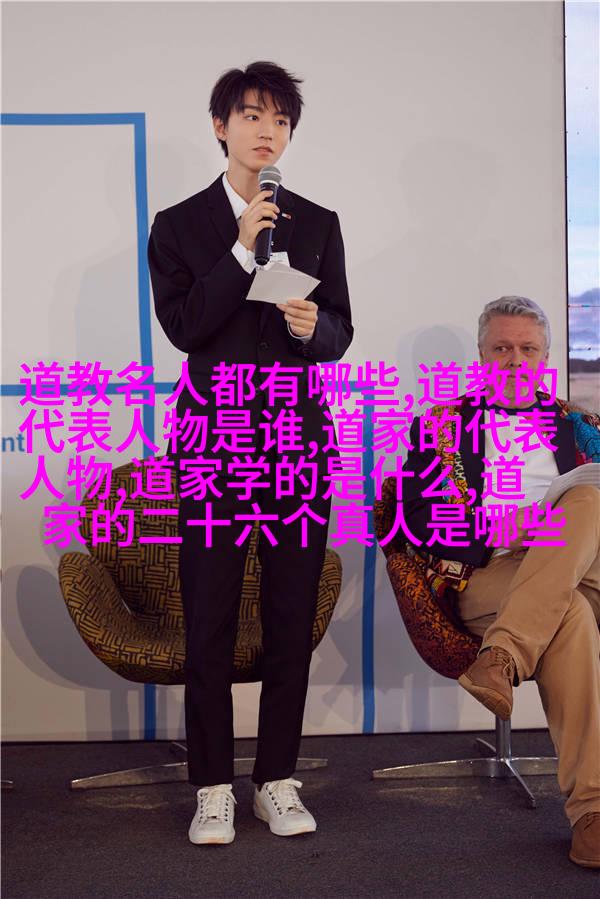
庄子问完后,拿过骷髅竟当成枕头,沉沉睡去。谁知,半夜时分,骷髅入他的梦来解答这千古之问:
从您的问话看,您像是位辩士。但您说的那些都是活人才有的负累。人一旦死后,上下级的管辖没有了,四时的劳役解除了,从容地随顺时间流逝,你估计纵使南面称王,也乐不及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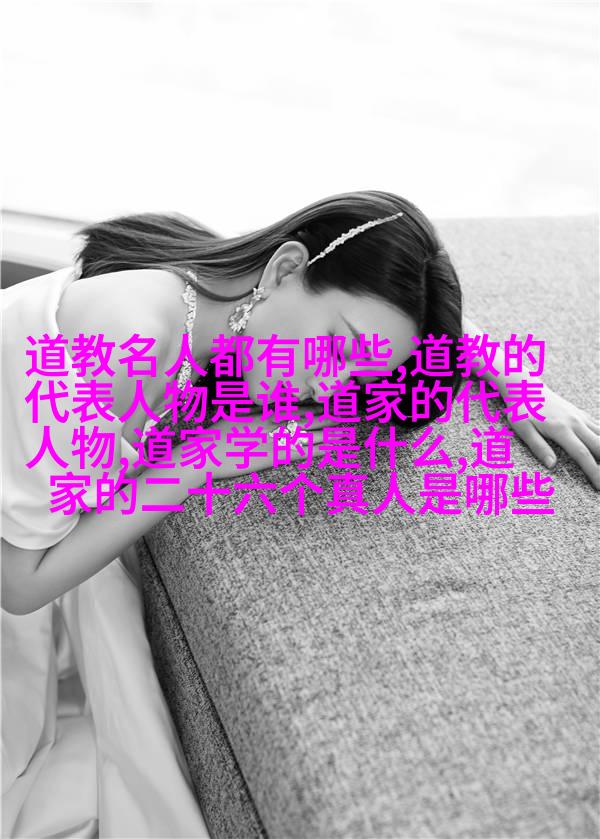
庄子不相信,说:“若是我让造物者将你复生,再送回到你的父母亲人、邻里朋友中去,你愿意吗?”
骷髅忧虑地说:“我怎能抛弃这君王般快乐而再次经历人间苦劳呢?”

这个故事很有名,也有多个演绎版本:《列子·天瑞》中的引述、汉赋作家张衡的《髑髅赋》,才子曹植的《髑 髏说》……熟悉道教经忏的小伙伴还会知道,在“放焰口”道场中也有两个唱段《金 骨头》和《银 骨头》,也是对庄子的遇到的演绎。
两者内容相仿、旨趣趋同,其《金 骨头》叹词如下:

昨日荒郊去玩游,
忽见一伏,
白骨白骨,
眶眼儿瞌睡。
风吹败叶,
满径满径堆愁。
饿鬼饿鬼,
无食无食只等死。
雨打风筛今几秋?
恨悠悠。
不闻人语,只听惟听溪流。
在原初故事里,这具客死街头的骷髅生前当过国君可能性微乎其微,它所谓“王乐”也只是一种想象。这具客死街头的人类形态已经消逝,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生”对于他们来说显得遥不可及。在这样的背景下,这具顽固存在着但已非存世之体的人类形态,不禁引发我们思考:在历史的大潮汹涌澎湃中,有多少生命被淘汰,有多少灵魂被遗忘?
这种思想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即易经中的性格分析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格,就如同每一块石头都拥有不同的纹理和颜色。而易经通过其独特的手法,让我们了解这些不同性的力量及其可能产生的心理状态。
例如,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往往被认为具有柔韧和温婉,但同时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强烈和坚韧。这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地球,每个角落都隐藏着未知,却又充满着生命力的泉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能够找到那份平衡,让自己既保持柔软,又不失刚毂?
这种探索促使我们更加关注于内心世界,而不是外界浮躁的事务。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超越现实,把握住那个更高层面的东西——即便那只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情景,如同乡土里的那些传说一样。
然而,当我们站在历史长河的一端,看向远方,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似乎变得模糊,而现在却变得清晰。当我们试图以现代眼光审视这些古代智者的言论时,他们的话语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将我们的内心深处映射出来,使得过去和现在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情感联系。
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一些基本的问题永远不会改变,比如人类对于死亡本质探讨以及对于生命意义追寻这一切始终存在。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以后的道路将会更艰难,更复杂,但最重要的是保持内心世界的一致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路径,并且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