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论全真道戒律的生态伦理价值

在金世宗大定年间,王重阳以其高迈不群之智,出入三教,一洗传统道教之陈弊,慧然独悟,陶冶熔铸,从而在道教史上开创出一种全新的道教新型式——全真道。从道教思想发展的历史看,以性命双修、功行合一为之途径,以明心见性、返璞归真为终极的生命了证为基本特征的全真道的出现,无疑标志道教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正是围绕着明心见性这一根本目标,全真道展开其全部戒律系统。
本文旨在对自王重阳创教至全真七子宏教这一早期全真教学戒律形成过程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一阶段,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全真宫观系统尚未最终形成,其戒律具有区别于后期的一些特征。本文还试图探讨全真戒律系统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早期全真学若干戒律体系考察
从全真的立教与发展的一般历史考察来看,早期 全真的学 戒律体系形成与 全真的学 立宗旨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宗 教 戒律是宗 教 团体为了维持内部生活而制定的行为准则,其目的便是实现 宗 教 的终极超越目标。在中国 道 教 史 来 看 道 教 很 早 就 生 产 了 自 己 独 特 的 戒 律 系 统,从简朴的小数到繁杂的大数,一直到三百零八条[1]。真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在此等戚事身外衣下,每个信徒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莫不有章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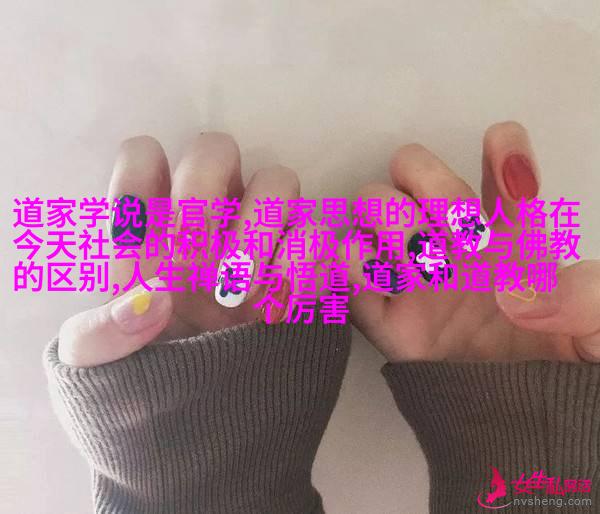
二、关于王重阳开启时期两种 全 真 学 戒律文献
综合考查早期 全真的学 戒法产生和演变的情形,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内,全真的学 戒法表现出了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由简朴到初具规模,再由零散整合成完整体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变期间,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全真正始祖马钰及第一代七位嫡传弟子刘处玄、丘处机等都对整个戒规体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 全真的 开创者之一,被尊称为“帝君”的王重阳并没有像人们预想中的那样,为他所创建的这套独特信仰提供了一部详尽严格的制度化规定。他虽然仅仅在陕西和山东弘扬了短短三年,但他的影响力却广泛且深远。他不仅点化并培养了七位嫡传弟子,还成功地建立起了一系列群众性的组织,如宁海、三灯会等,这些组织需要有一套规范来维护秩序,并确保它们能够协调相互之间。
现存《古籍》中确实存在一些类似于 王 重 阳 名下的近似戒规文献,比如《重阳立训十五论》、《帝君责罚榜》[3]。其中,《重阳立训十五论》就列出了十五个方面,对信徒日常生活作出了规定;《帝君责罚榜》的十条惩罚法律更显得直接而具体,它们似乎是一种针对正式成员或寺庙居民制定的规则,而非一般公众。而这些文本似乎更多地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具体行动达到精神上的境界提升,而不是简单地遵守某些禁令或规矩。此外,这两个文本也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心灵追求以及对于个人修炼道路上的严格要求,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坚持一定的心灵状态和行为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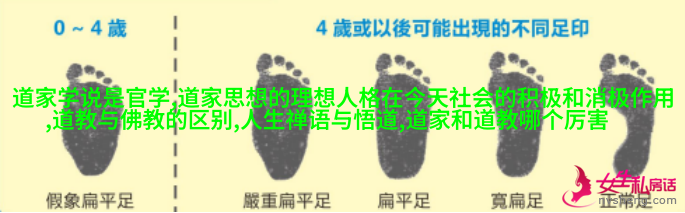
我们注意到,《帝君责罚榜》的十条法律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因为它们涉及到的问题像是说谎、高谈阔步,以及做事情漫无目的,都可能导致被逐离社区。这表明这些法律主要针对那些居住在寺庙或者频繁参与寺庙活动的人士。而对于那些只偶尔参加寺庙活动或者完全保持个人隐私的人来说,这样的法律可能并不适用。此外,由于这些法律很难被普遍实施,而且由于缺乏执行机构,使得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因此它无法成为任何社会结构稳定的基础部分,只能作为一种特别情况下的临时解决方案使用。
总结来说,在探索原始材料以理解原始文化时,我们发现许多文献往往包含着多层次含义,有时候甚至难以将其视为纯粹意义上的指导原则。不过,在现代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去解读这些材料背后的文化哲学思考,并根据当时社会背景,将它们置入更宽广的地缘政治框架中去分析,从而获得更全面认识。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古代文化,那么必须考虑他们时代的情况及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对于世界和人类存在意义的一种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回顾过去,同时也要努力将我们的知识应用于现代社会的问题解决上去,让我们的学习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更加有用。这就是我认为学习古代文化应该怎样进行的一个例子。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分析方法,并且希望你能分享你的想法,我相信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