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们不要太“自私”地用我们的善意和保护传统的信念去限制研究对象真心情愿做、积极主动的事情,因为我们可能会“表错情”。危机也许是生机。

采访人:张应华 记录人:尚建科
张应华(以下简称“张”):刘教授,您参与的仪式音乐研究领域,能否就当前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分享您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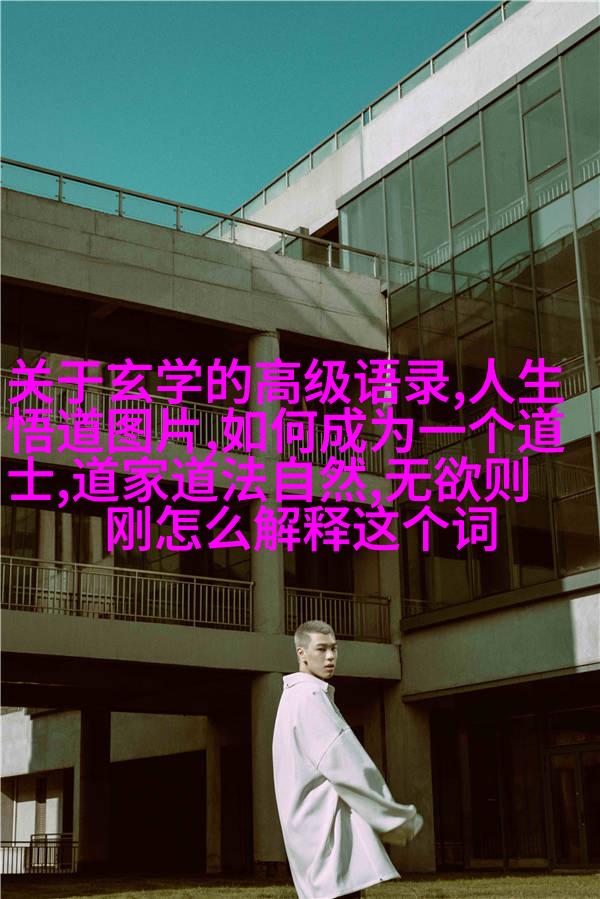
刘红(以下简称“刘”):我不敢说自己有资格或代表性来谈论仪式音乐研究,但可以分享一些个人感受。
您认为为什么仪式音乐研究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我们过去在笼统的“传统音乐”或“地方民间音乐”的概念下进行田野考察与研究,与现在较为广泛提到的“仪式”概念相吻合。或者说,我们今天形成的仪式音乐研究热点中的“仪式音乐”,其概念包容性较广。这个原因在于通常所说的仪式音乐涉及神圣部分和民俗部分。我觉得,我们缺乏认识的是民俗部分中的某些特性,如约定俗成、通俗、风俗等,其中包括了某种程度上的秩序和规则。而将这些具有规则与秩序活动放到仪式中,便表现出它们与儀礼相关联。这意味着我们之前认为是传统音樂或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一些文化现象,其实包含了儀禮的一些准則或符合某些儀禮概念。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一些专注于此类研究的人士以及专门机构推动,比如上海音楽学院设立的「儀禮音樂研究所」实施众多相關課題,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曹本冶教授主持過一系列相關研討计划等。
以上两大因素促成了現今學術界對於儀禮音樂之熱門化趨勢。

尽管如此,在未來相关研讨中,我認為應該注意,不要对任何现象无原则地归类为「儀禮」。因为具有特定的特征并不一定就是特别意义上的「儀禮」。而且不能把「儀禮」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框架套用所有文化现象,这種泛化是不好的。如果没有明确它属于何种范围,并且如何表达非一般性的现象,那么我們會說吃飯也有礼节,但是平常吃饭就会被视作是一种正经八百严肃认真的「仪礼」,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在我的理解里,不能泛化,而应该强调标准,有条件,有要求。如果没有要求的话,随着时间流逝,它们便不会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