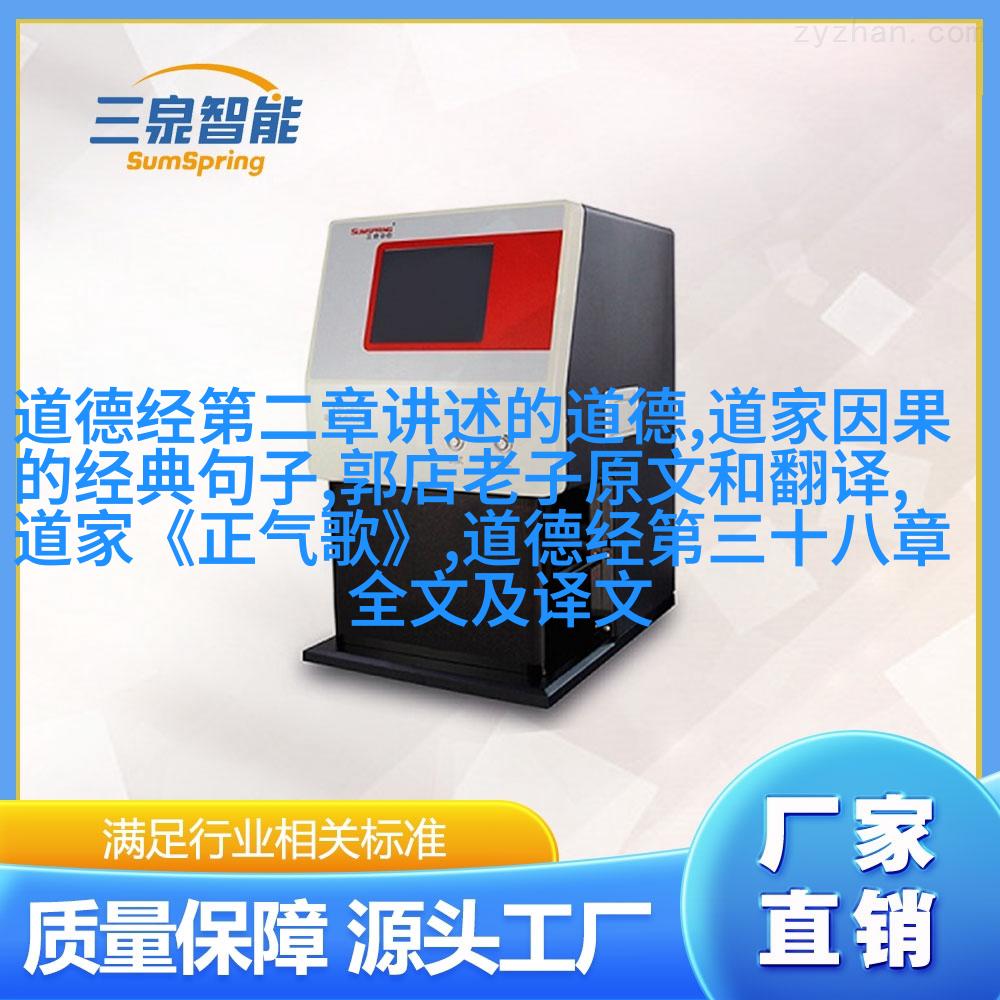我在二十七日下午结束了年终的账目安排,二十八日便开始准备迎接团年。到了三十日下午,我在山门外设立香案,为本宫前辈和后辈各派霞灵牌位进行巡照,并高举普板。经师和高功在大殿搭起衣物,随着“召请”的声音去山外招呼道众。监院则负责拈香,摄召完毕后,经师引领道众,而监院带着牌位前往祖堂安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请羽化道众回常住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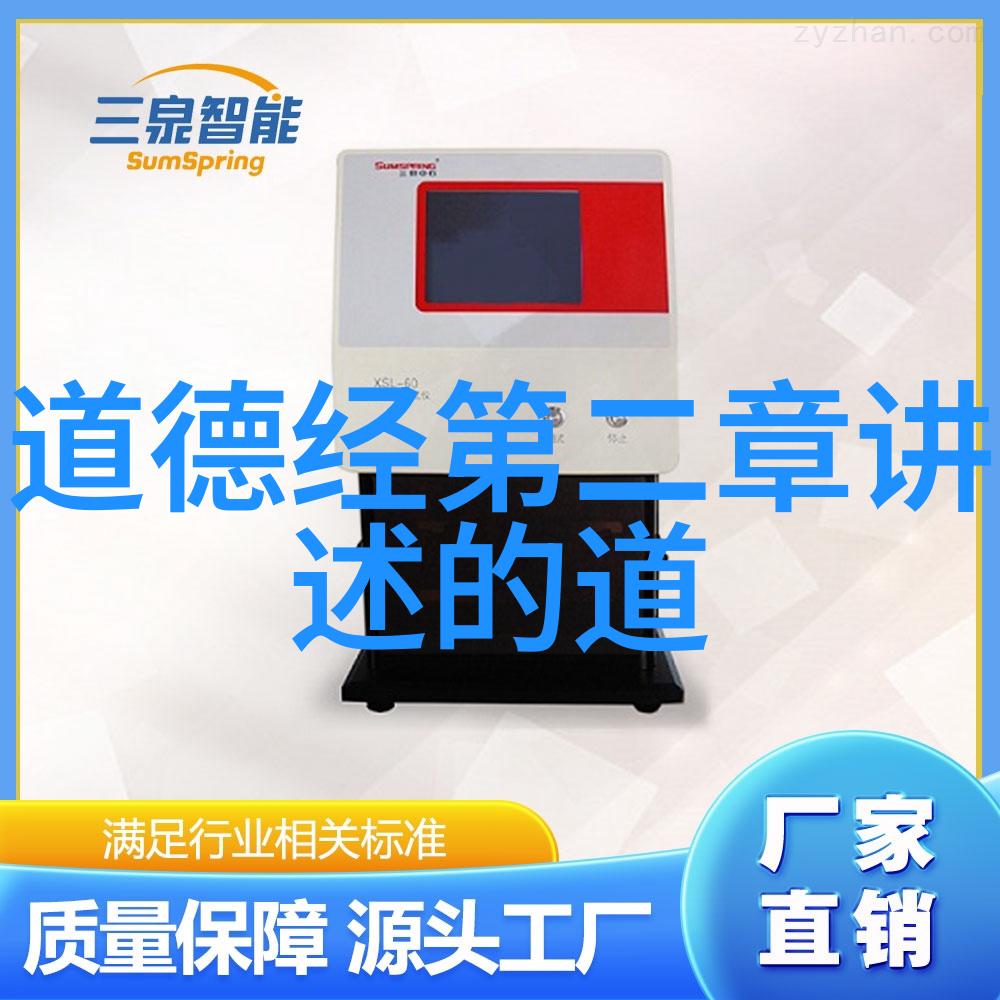
每个殿主都前往厨房请供,而寮房则提出了表格。在晚课之后,我们出坛祭祀孤神,然后转向天尊。在下殿后,经师用韵律打响法器,将监院带到各处神位前进行普表。我吃过晚饭稍作停留,便安排执事排班,请监院进入大厨房“接灶”。经师随后去了客堂享用果品茶饮。餐食完毕,我们便开始发动鼓行祝寿仪式。这一系列活动完成后,我们云集于祖堂。
初一清晨,当子时敲响静音时钟,我喝了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早课结束后,我们又出坛、祝将、转天尊,在早课完成之后,我为喜神点燃香火并设立香案,上供“喜神”牌位。此刻寮房备好了一个装满花生、核桃、枣和钱等物品的小斗,用红纸封好备用。当我们接待喜神时,每个人都会持着香绕至喜神案前插上一炷香,再做三次叩首,然后快速返回大殿。此时巡寮人员点燃长鞭炮跟随监院回到大殿,并将喜神牌位交给殿主供奉。大殿内外爆发出欢庆声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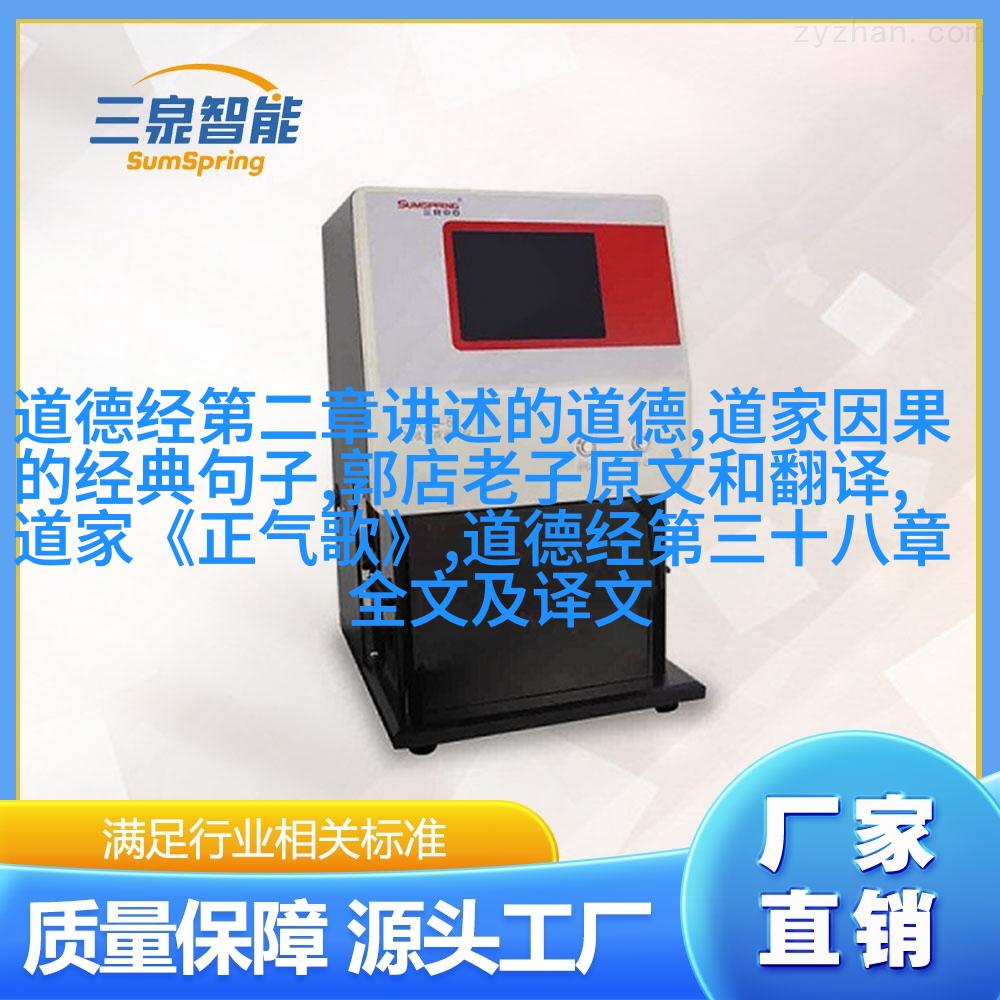
接着我问:“喜神回来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回来了!”于是我抓破红纸,大把地撒出斗中所有物品,再问一次,“来啦”,再撤掉一次,“回来啦”,最后三问、三答、三撒完毕。我东抛西扔,一把扔得飞快,又是前抛後扔,不断地乱撒,有人拥挤而争相抢夺,最终我扬起手轻松地撒尽所有东西,让巡寮人员收拾残余。
然后我喊出:“给喜神拜年。”大家纷纷站起来朝上做三次叩首。而知客喊道:“大家给监院拜年,”而寮房则喊:“监院给大家拜年”、“大家团拜”。这场风雨般的互相拜年的气氛让人兴奋不已,无论磕头有多快或慢,都被卷入了这份共同欢庆之中。一切顺利完成之后,我作为学生向先生表示辞岁之意,而其他道友也相互之间表示辞岁之意。

此刻正是我发动鼓行祝寿科仪的时候。我站在祖堂里,与其他人一起参与这一庄严而充满期待的仪式。一旦结束,我们便分散去各自寝室休息。这五天里,每天清晨与傍晚我们都要出来聚会。不过,由于腊月二十四日之前已经迎来了新的一轮生活规则,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一切动作变得更加庄重正式,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变化。
从腊月二十四日起,每个人都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更换位置,而是根据自己的职责定居于十方堂或云水堂,这种定居状态被称为“挂年单”。直到初六早上的饭点才解除这一状态,让我们重新获得自由行动权。

正月初五,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之一——上坟。那一天下午,我看到人们准备了盛宴和祭品,将这些食品分配到每个家庭,同时也是对逝者的一种纪念。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每个人都穿戴整齐,一副庄严肃穆的情绪。一如既往的是,那些熟悉的声音,那些温暖的话语,它们似乎能跨越时间空间,对那些已经离世的人致以最深沉的情感。
自从接受驾驭指令以来,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前往皇经殿进行朝圣活动。而在正月初一至九期间,不仅如此,还需要额外参加皇忏活动。如果遇到庚申或者甲子日期,也会特意增加一些特别的敬礼,比如向星辰致敬。但无论何时何地,只有一件事情始终伴随着我的生活:对那些永恒不变的事物保持忠诚与敬畏。而当夜幕降临,在距新春只有两天远的地方,我们展开了一场盛大的祝寿筹划,为即将到的春季预演最美好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