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七日下午结束了年终的账目安排,二十八日便请来团年客人。到了三十日下午,我在山门外设立香案,为本宫前辈和后辈各派霞灵的牌位进行巡照,并高举经师与监院前往“召请”(摄召)。摄召完成后,经师引领道众,而监院则携带牌位前往祖堂安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请羽化道众回常住过年”。各个殿宇主持者前往厨房准备供品,而寮房则分发表单。晚课结束,我们出坛祭祀孤魂,然后转向天尊。下台后,经师开始打法器,将监院带到每个神位前进行“化普表”。静默之后,我们吃完晚饭稍作停留,便由执事排班邀请监院到大厨房“接灶”。经师随后去了客堂享用果茶。一顿饭过后,我们开始行祝寿仪式。完成这项仪式之后,我们云集于祖堂。在此过程中,大众纷纷给予监院辞岁之礼,监院也给予大众辞岁之礼,而道众们一同辞岁。大学生们对先生表示辞岁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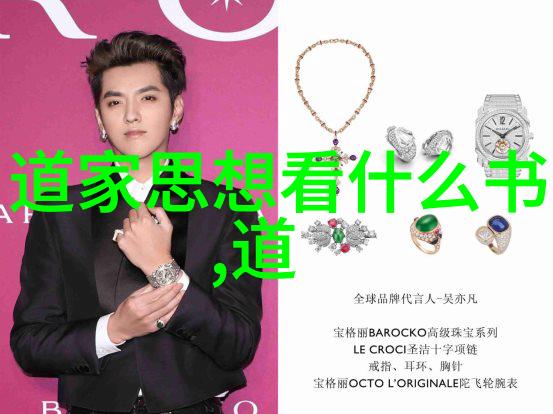
初一子时,我开启了静谧的气氛,与大家共享“胡辣汤”。早课结束后,我们出坛、祝将、转向天尊,再次进行早课。课程结束时,我们迎来了喜神,并为其上香。我负责将花生、核桃、枣和钱等物品装入斗中,用红纸封好备用。当接喜神时,我与其他道友轮流插香于炉前,一边叩头一边拔出香燃起火焰,然后快速回到大殿。我再次返回山门外,将喜神牌位供奉妥当,此时巡寮人员点燃鞭炮伴随着我的步伐进入大殿。在那里,我将斗中的物品撒散四方,不断地提问并回答,最终撒尽所有物品。我最后一次问候:“喜神回来没有?”大家齐声回答:“回来啦!”然后我抓起斗中的物品再次撒散。这场景不断重复直至所有东西都撒完。此刻,每个人都围聚在一起,无序地磕头,有快有慢,你推我拥。
拜访喜神之后,我要求大家朝上三叩首知客喊:“大众给监院拜年”,而寮房响应喊:“監員給眾人拜年”、“眾人團拜”,接着是抢夺金币和拜年的混乱场面。在这一切活动中,要营造一种观感,如同万象更新,满怀欢乐,不论磕头还是移动,都显得无序而快乐。一旦收获了喜神,我便要求大家排队给我先生拜年。此外,还有许多朋友相互之间交换新年的问候。

正式开始庆贺仪式期间,由经师敲响鼓笛,让执事按科庆贺云集于祖堂。而且,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当我们的主人驾临之后,每个人都不再动弹,只有挂上任务卡片的道友,在十方堂或云水堂居住,被称为挂年单。初六清晨,当食盒准备就绪以及祭品菜肴摆放在高灶上的时候,大家便开始忙碌起来。这包括对亡亲的一份祭品,也就是所谓的普饭。而衣冠整洁的大多数道友,以及穿戴整齐的地界幡手持幡杖跟随著高功到达祖堂,那里存放着被摄召出的牌位。当这个时候出现,又是那个熟悉的声音:拍打法器声响彻空旬,同时导游们依然穿梭不息,他们正要去找那些遗失的人类灵魂。
他们穿越时间深处寻找那久远已逝去的人类灵魂,每一步都是寻求平衡与和谐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还会根据月亮走势来决定他们要去哪些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隐藏在暗影里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只属于他们知道的人群。

自从接驾以来,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登顶皇经殿。在正月初一至九之间,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参加皇经活动,然后下午则是皇忏;若遇到庚申或者甲子日期,则需要额外加餐敬拜星辰;到了第三个月夜,即十三夜的时候,如果是在星期二或者星期五,则需特别增加几句赞颂词以示敬意;到了第八晚,即即将迎来的新春佳节,那么就会举办一次盛大的祝寿宴会;而到了第九天天明,那么我们又会举行一次庆贺典礼,以纪念往昔荣耀的事迹。
这样的生活方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春分节气过来,当那时我们会一起踏上旅程去探访那些埋藏在地下的先人们,这也是我们的传统之一——清明节或十月第一日,上坟缅怀故人。不过,从今年开始,一切似乎都变了样,但却仍旧保持着古老习俗的一致性——虽然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么简单了,但人们依然希望通过这样一些行为来维系彼此的情感联系,让历史继续延续下去,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一样,是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界限的情感连接,是一种让人类心灵得以释放并找到慰藉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