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追求学术深度、坚守传统信念的同时,不能忽视研究对象的真实意愿和积极参与。正如危机可能是生机一样,我们的研究也许会因误解而偏离目标。现在,我将以第一人称重新表述这段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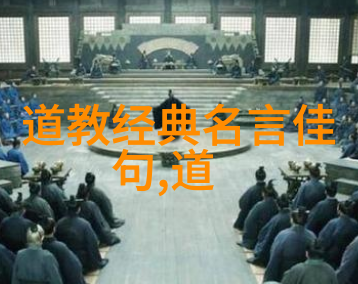
我认为,在我们的仪式音乐研究中,我们有时过于自私地使用自己的学术良心和保护传统的信念来限制研究对象能够做的事情。这可能导致我们“表错情”,即误解了他们的情感和动机。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道士能一眼看出问题?这或许可以从自然环境中找到答案。在自然之境中,道士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掌握了一种独特的洞察力,这种能力使他们能够迅速识别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然而,在我们的仪式音乐研究中,我们往往缺乏对民俗部分“俗”的认知,即那些约定俗成、通俗、风俗、俗风等方面。这些“俗”实际上包含着一定的秩序和规则,有时候与仪式密切相关。
此外,一些机构,如上海音乐学院的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一系列计划,也为仪式音乐研究注入了活力,使其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

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谨慎对待将任何现象归类为“仪式”。我们必须明确该仪式是否具有特定的性质,并且它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非一般性的特征。如果不加区分,就像把每天例行公事都当作严肃认真的仪式去分析一样,那么这种泛化是不恰当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研究保持其科学性和深度,不至于陷入无原则的泛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