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瓷器已经达到了一种宁静典雅、含蓄自然、清新质朴的完美境界,如同春水明月,绿云薄冰,让人对美产生了无限遐想。我们既惊叹于宋瓷的完美,也要探索那隐藏于表象之下的精神世界,这是理解宋瓷精神的钥匙。郑樵在《通志》中提出了“制器尚象”说,他认为人们制器既是为了实用也是为了“有所取象”,即有所寄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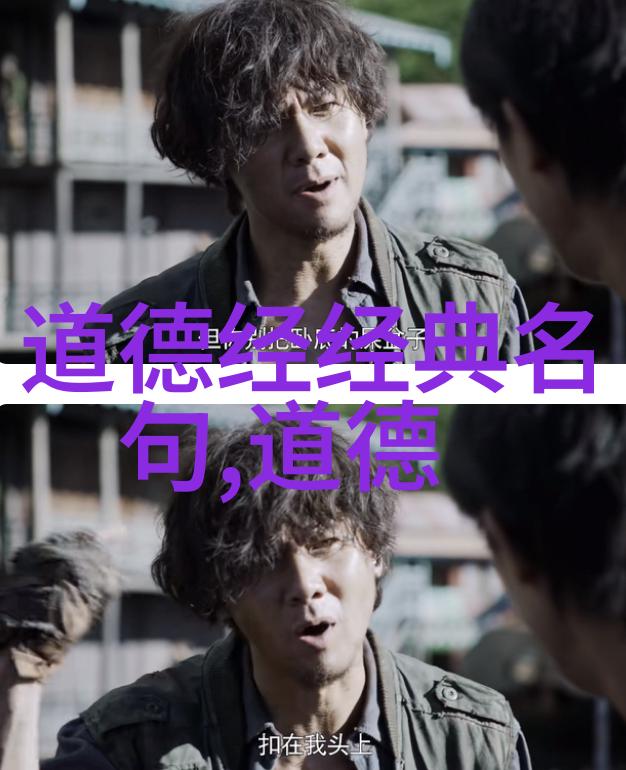
《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宋瓷则展现了道器合一中国艺术最高境界,既是器,又是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如何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随着立国初期实行偃武修文政策,整个社会文化教养极富,并沉醉于“郁郁乎文哉”的氛围中。此时,统治者大力推行和崇奉道教,使得它得以深入发展。

文化传播往往诉诸于符号。瓷器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具,也成为了传播思想与文化物质载体。因此,我们将宋代瓷器由造物自然生成的造型提升到更高层次来认识。
在多次战争后几乎每战必败的情况下,与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交锋,最终导致割地赔款、送礼求和。唐人的气概已荡然无存,而宋人则收回了对外界企盼和搜寻的心态转向内心反视与自省,以调息与自控为导向,将人的审美情感过滤并提纯至极致。这使得理学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引导个体探索内心世界,从而将人的审美情感过滤并提纯至极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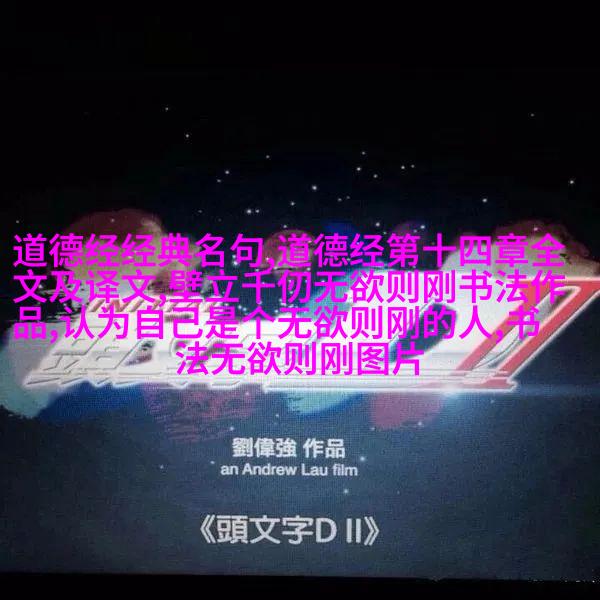
修文偃武国策及疆域收缩让宋人的心灵变得内向,同时也使其文化变得温文尔雅、婉转妩媚、精致细密,其艺术特质也倾向注重意态神韵和典雅平淡。正是在这种审美背景下,梅瓶等作品被创作出来,它们如玉立的少女娇艳但不轻佻,有着端庄妩媚的情趣,让人神往。在曲线和直线之间穿插变化,是一种追求内敛静默与圆润丰满相结合的手法。而这正好映射出唐代追求外部事功个性的不同风格,以及他们对于外部事功个性追求的一种表现方式;相比之下,梅瓶则是一种内敛、羸弱且符合返璞归真的理念,它们通过造型摆脱了以物役心的心理桎梏,使心灵得以解放和净化,最终达到人与宇宙浑然一体,即达到了某种境界,即达到了“道”。
另外,在釉色装饰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老庄美学得到进一步阐扬。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对自然本色的崇尚成为最高审美标准,因此追求釉色之美去除繁缛纹饰鄙弃雕琢伪劣,只朴素自然之美才能称为真正的大师级别作品。而天青作为代表,便因为其天然本色,被贴上了 道家的标签。“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所以天青便成了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一个颜色,更直接地触及到人类对于宇宙万物本原状态的一种思考。

此外,在釉面的纹理上,如冰裂纹这一形式化比喻,其状如冰开裂时形成的纹理一样晶莹透亮气势磅礴变化无常,这些裂纹原本是制瓷工艺中的一个缺点,但却被巧妙利用,将残缺变为奇迹,将失误变为珍贵,从而实现了一种从缺陷到绝技的地步。这一切都显示出了一种超越自身局限性的智慧,一种将不足变足够、一切皆可利用、一切皆可发挥的手段——这正是一门高超艺术手艺,其中蕴含的是一种哲学思维,那就是适应环境,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无论是在技术上的还是在品味上的,都充分体现了古籍中的哲学观念——顺应自然,无强迫,无刻板,而是自由流动,不拘泥于固定模式,这便是一门高超艺术手艺,其中蕴含的是一种哲学思维,那就是适应环境,不断创新,不断进步,无论是在技术上的还是在品味上的,都充分体现了古籍中的哲学观念——顺应自然,无强迫,No to rigid patterns, but free flowing and adaptable, this is a high-level art craft that embodies a philosophical thinking, which is adapting to the environment,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whether in terms of technology or taste.
最后,用钧窑花盆这样的例子来展示这一点,该花盆呈现出天青色以及玫瑰紫海棠红交织其中,“夕阳紫翠忽成岚”般千变万化,可见其独特性非凡。这背后的哲学深度就在于它完全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只能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是这样一个事物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力的自身追求,而不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个机构服务。这便是我国古代陶工们几百年来的智慧结晶,他们通过这些小小的事务展现出的深邃思考,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地方。

